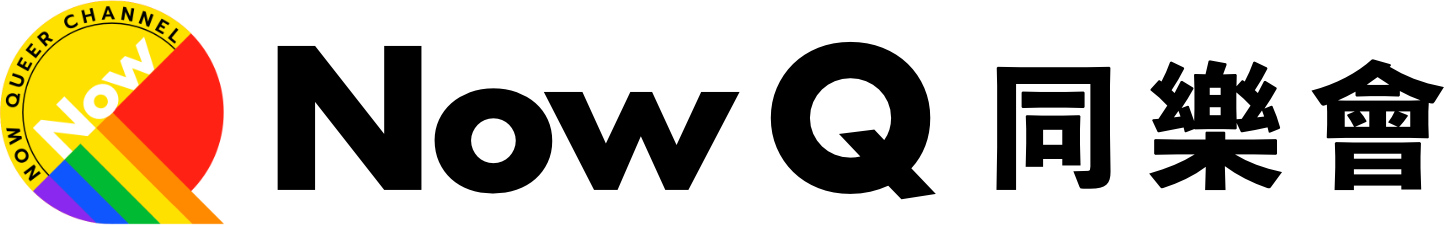文/羊羊
「全球在地化」是當前發燒關鍵字,為了延續既有的強項,推出同時反映時代與本土文化的精采封面故事《VOGUE》集結國際共27個版本,聯合推出全球性的主題「New Beginnings」。每個版本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「嶄新開始」的概念,以日出為共同象徵,代表對疫情過後的世界重燃希望。
隨著時尚產業的日新月異,為了符合更國際、永續與多元的目標,盡可能探索新型態的能源、擁抱廣大的國際資源脈絡,以及轉向更包容和諧的群策力工作型態。
《VOGUE》往後將會更著重在世界級、多元、跨文化以及屬於《VOGUE》的獨家內容。
「新」是初心 象徵著家鄉的名字
台東太麻里,在2000年1月1日的時候,是迎接二十一世紀第一道曙光的神聖之處。為了九月號封面,《VOGUE》來到了這個能夠見到第一道曙光的地方,為了紀錄被颱風肆虐連日豪雨後的天光。
阿爆梳著高馬尾優雅站著,布拉瑞揚直挺挺地矗立猶如雕像,兩人與布拉瑞揚舞團的一眾舞者,身上彷彿有著隱形的羈絆,默契十足。在台東崎嶇陡峭的地貌上,滾著翻騰的海浪,一幅宛如舞台劇,帶著極強張力的影像故事就此誕生。搭配著阿爆特別為《VOGUE》獻唱的15秒曲子,以山和海的名字為出發,她吟唱的聲調像浪花一樣溫柔,歌詞的意思是:「過來,過來,換你唱了。」

布拉瑞揚和阿爆是表兄妹,兩人來自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。這對相差九歲的排灣族表兄妹離家得早,對彼此的印象只能從親戚的口中模糊勾勒輪廓,直到布拉瑞揚回到台東之後,他們才拾起了對彼此的記憶:「那個小小身軀、長頭髮、很會唱歌的妹妹」以及「那個長得很像外國人、舞蹈很厲害的哥哥」。繞了一大圈,兩人現在都成為原民文化的創作者。阿爆吟唱出母語歌曲,更不遺餘力培育年輕原民音樂人;布拉瑞揚也在台東找到了棲身之所,跟一夥不太有舞蹈經驗的原民們從生活中衝撞想像,體現藝術。
人生說長不長,說短不短,但或許總是充滿意外的可能。面對生活的擺盪、挫折以及自我懷疑,布拉瑞揚和阿爆都恰巧選擇將原民根源作為永恆的繆思女神。
什麽是新開始?對布拉瑞揚和阿爆而言,新是初心,也或許象徵著家鄉的名字
阿爆:「在我的生活當中,生命象徵著新的開始。」
音樂從小就環繞在阿爆的生活裡,這件事情再自然也不過。外婆跟媽媽都愛唱歌,耳濡日染之下她就出落成了一個愛唱歌的小女孩。她五歲時還不會看字,卻已經在工地卡拉OK唱出了林淑容的〈我怎麼哭了〉。小時候的她因為唱歌得到了大人的鼓勵掌聲,被正向激發,唱歌這件事情變成可以帶來成就感的事,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。她笑說,或許是因為比較早失敗,後來會比較清楚自己在做的事。
「我23歲拿了第一個金曲獎,後來才知道,人生不是因為你獲得了最高的榮譽,往後所有的路途就會順遂。或許因為很早就跌過跤,所以現在一點點的鼓勵我都非常感激。對阿爆而言,每首曲子都有其獨特意義,拿下2020年年度最佳歌曲的〈Thank You 感謝〉當然是其一。
今年年初,阿爆的媽媽離開了,面對長輩和至親的離開,阿爆坦言這是不容易的關卡,她說:「人跟人之間相處的緣分很短暫,陪伴一個人度過他生命當中最後一刻的時候,這個過程會讓我對生命有不一樣的體會。所以我現在想要把握每一天,從很小的事情開始。認真過生活,好好對待身體和心靈,生命其實可以自己定義。」她愛上了聽媽媽以前收藏的黑膠唱片,其中有一首老歌謠叫做〈再見心上人〉,是首浪漫的曲子,被古老的調子轉音圍繞,類似演歌的唱腔,搭配只有一把吉他的純樸美感,阿爆被這首歌深深吸引,也開始思考把老一輩的東西加入當代元素,變成大家喜歡聽的樣子。
就像布拉瑞揚說的:「妹妹是我認識最誠實的人。」或許因為這樣的誠實,阿爆的言行也被網友譽為正能量女王。前陣子有網友評論她的膚色,她高EQ的回答造成熱議。
阿爆說:「網路這個東西就是這樣,上面的名字就是代號,有暱稱的時候可以不設限傷害別人。因為是匿名的,我不太會理會,雖然我不會因此受傷,但有些人可能會因為這樣的一句話明天就去預約美白針。有千千萬萬的人對你品頭論足,你不可能改變你自己,不要因為別人說你怎樣就飄移。這一輩子跟你相處最久的就是你自己,所以不要去理會別人的評價,這是我一貫的態度。」不畏懼他人言語,因為阿爆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誰。
瀏覽阿爆的臉書和Instagram,會發現她的社群媒體現在就像是原民文化的資料集散站,她笑說自己的生活真的充滿了原民文化,她像是一顆恆星,逐漸拉攏聚集了越來越多相同磁場的人,尤其音樂這塊更是。她主導的那屋瓦計劃發掘了許多優秀創作者,今年入圍金曲的žž瑋琪就是其中一位。

布拉瑞揚:「做自己是一輩子的功課。」
他是台灣表演藝術界無法替代的存在,被美國舞蹈雜誌稱為「擁有強大而傑出的天份」,征服過紐約、溫哥華、法國等世界級舞台。在紐約闖得風光之際,毅然決然於2014年返回台東,創立布拉瑞揚舞團,現在他在台東糖廠的老廠房裡領著一票非典型舞者,並拿下連續兩年的台新藝術大獎,在生活瑣碎的切片裡找最真摯的藝術。
布拉瑞揚說,在諸多原因中,最關鍵的還是2011年他在紐約林肯中心牽著瑪莎葛蘭姆舞團舞者謝幕時,突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傷情懷,他突然好想念父母,好想念家鄉,他當時心裡想,如果我在台上牽著是自己家鄉的舞者,那剛有多好。
「人年紀越大就會慢慢走向自己的文化。在台灣做一個原住民是會迷失的,雖然我1995年就改了漢名,意識到自己要成為布拉瑞揚,但我整個二十年過的漢化,也可以說是洋化吧,每天好幾杯咖啡,視覺和想像我離我自己越來越遠。」他想,那我就回台東吧。其實一開始帶著有點想要逃避的思緒,因為生活變得不如預期。他回家,關起門來,自己做自己的事。2015年初,布拉瑞揚找到台東糖廠的倉庫,創辦舞團的夢想在此生根,只是沒想到這關起門來找自己的舉動,卻被更多人看見。
布拉瑞揚還在台北生活時總是戰戰兢兢,因為所有作品的創作、人設的表現不只代表自己,還有雲門舞集。布拉笑說:「人家都說我以前有包袱,我不抽菸、不喝酒,連買個咖啡都要很體面的樣子。我還開始修正講話的方式,不可以有口音。從部落離開後,我一直偽裝成別人,因為我看起來太不一樣了,要很辛苦才能融入這個社會。」後來布拉瑞揚到了紐約,前前後後待了六年,他本來以為自己一輩子都要住在紐約了,因為這是他一直想要的生活,沒有壓力做自己,可以一直創作。紐約四通八達的多元有益於創作者,布拉瑞揚喜歡漫無目的地在紐約散步,也喜歡坐地鐵,雖然髒亂又臭,但可以看到各種人種。「在紐約總是會發現自己的渺小,而那樣的渺小讓我很自在,因為沒有人在乎你是誰。你會在地下鐵發現很多有才華卻沒被發掘的表演者,只能在地下鐵勉強餬口演奏,即便如此,他們還是很開心,那是真心喜歡一件事情的模樣。」
即便這麼喜歡這座城市,但還是想家了。於是布拉瑞揚買了一張機票,回到的不是台北,而是家鄉台東。那些在台北的包袱,以及在紐約的執著,都在回到台東的時候變得輕盈。布拉瑞揚跟一群幾乎沒有受過舞蹈訓練的人一起跳舞,他變得放鬆,因為把自己完全歸零。他再也不需要武裝自己,既然舞者什麼都不會,他也不需要設限,全部打掉重練。布拉瑞揚變了,他的人和作品都變了。

布拉瑞揚跟阿爆一樣,知道唯有誠實面對自己才是創作目的,這也是這一對表兄妹靈魂上最契合的主因。「我一開始是成為舞者,後來成為編舞者,然後我要成為布拉瑞揚。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做自己,但做自己到底是什麼?我又是誰?回台東之後我開始明瞭了,這其實是一輩子的功課。」本來在紐約找自己,追尋一種西方的舞蹈形式,但後來發現,這初衷原來在自己的家鄉。「現在我很喜歡的一個浪漫的想法就是,我還在回家的路上,進行式。」布拉瑞揚這麼說。